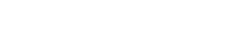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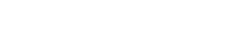
【情系科学】热塑剪切带(II)
编者按:国际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物理科学部原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原理事长白以龙研究员,因病于2024年5月9日9时21分在北京逝世。白院士曾在2020年撰写了回忆录《求索(八十年的个人经历和感悟)》,其中不少篇章谈及他从事科研的体会,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复杂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和正确的判断能力,对年轻学子颇有启发意义。本刊特此选取其中的第五章文字,分三次连载(编者在排版上做了一些调整),以飨读者。
热塑剪切带(II)

3.A sharp boy
过完了暑假,我离开了牛津,来到了剑桥,跟着Bill Johnson干,这时,非常需要重新打开局面,所以一段时间里,我把对热塑剪切带研究的这件‘私活’搁置了下来,直至我在Bill Johnson那里做完了几件他交给我的活儿,站稳了脚跟,我才决定,把我的热塑剪切带研究的初步结果,系统、完整地整理出来,形成一篇正式的科学论文,并想把它发表在J Mech Phys Solids 上。
J Mech Phys Solids是当时世界上固体力学领域最权威的刊物,那时,它还是个双月刊,一年只出6期,每期也只有少数五、六篇文章,一年才发表三十几篇,大名鼎鼎的R Hill曾是这个刊物的主编,那时主编则是Hopkins。
我把整个工作从头到尾又仔细地整理了一遍,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篇完整的、正规写的英文科学论文,又是投向英国人掌控的权威刊物,绝对不能让刊物编辑一看,内容缺少科学性、文字又不通,就打回来。几次修改之后,我请Bill Johnson的女秘书帮我打字成正式的稿件,终于在1981年的春节期间,把稿子寄给了主编Prof Hopkins。
我焦急地等待刊物的反馈,但是,好像是我回复了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之后,我的稿子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信。那一段,我如坐针毡。加上,到这年的八月份,我在英国的两年访问学者的期限就要到了,我当然希望,在此之前,我的文章能被接受。
可能是Bill Johnson察觉到了我的焦躁的情绪,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此事。我说,我寄了那篇稿子给J Mech Phys Solids的主编Hopkins,但是,久久没有消息;我记不得,是否后来还给了Bill一份我的文章的复印件。但是不久后的一天,当我去见Bill Johnson时,他对我瞪了瞪眼睛,然后问我说:你寄给Hopkins文章,以及回复他问题的时候,你都说了些什么。说实在地,即使在那时,我也记不得我是否说过了些什么特别的话。 不过,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认为,我采用的分析方法,在流体力学里几乎是人所尽知的常识,但是,做固体力学的人却知之甚少。我不知道,我的这种潜意识,是否在我寄给Hopkins的文字里有所流露,而这位英国人,又做了哪些他们的理解。反正,Bill听完我说的情况,却笑着对我说:Hopkins对他讲,Bai是个a sharp boy!就我的英文水平来理解,sharp是一个可以有各种各样、好坏各异的中文解释的英文词,但是,看到Bill 说话时笑眯眯的样子,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褒义来理解,于是,当时心中颇有些轻松。
到那时,我才知道Bill和Hopkins是朋友。现在,在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我上网查询Hopkins,又才知道Hopkins在那个时候是个大忙人,在UMIST任教,却又身兼数职。而且不幸的是,他在1982年的春天突然去世,还不到65岁!
我的文章,也正是在那个春天完成了最后的修改稿,然后被正式接受发表的。在稿子的整个修改过程中,涉及了不少准确表述的讨论和推敲。我现在依然能清楚地记得,我对简单剪切(simple shear),和纯剪切(pure shear)之间差别的认识,也就是在此修改中,才被严格澄清了的。
4.准定态热塑剪切带 —剪切带宽度
我于1981年夏天回到了国内。离开力学所两年,所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离开的时候,刚刚组建的十六室——材料力学性能室,已经成为包括了多个研究组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室了。我按照老赵(士达)的意见,参加了他直接领导的研究组,也就是以轻气砲为主的材料动态力学研究小组。我跟着他们放炮、做航天部一院十四所委托的材料的崩落(spall,也称层裂)试验。虽然在我去英国之前,在我们所做的文献调研中,关注到了材料的崩落是一类非常独特的动态破坏现象,但是,那时没有感性认识,文献中也仅仅是些经验公式而已,所以,直到若干年过去,我们积累了不少的实验观察和数据,并设计和实现了两个全新的实验之后,我们开始了另一项长达约二十年的工作,我将在下一章对此做专门的回顾。
实验工作总是有间歇的,那时,我脑子里的问题依然是热塑剪切带。我觉得,我虽然解决了热塑剪切不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整个国际学术界,也包括我自己,依然没有阐明失稳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它一定会发展为事后解剖在金相中看到的,几到几十微米宽的剪切带?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电子数字计算机,但是性能很差,做个常微分方程组的解,也要靠自己编龙格-库塔法的程序,计算机还老出故障、出错。因此,很难通过数值计算,来揭示热塑剪切变形在失稳以后的整个演化过程。这样,通过深入的物理理解,以形成合理有效的简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
我先后和俞善炳和郑哲敏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搞清楚的事情。经过几次讨论和尝试,我们发现,可以从时间过程的另一个极端——终态来切入。人们(包括我自己)通常都是沿着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考察问题的,例如,从一开始的均匀变形,如何随着加载的时间,发展出了不稳定性。现在,我们则先不管热塑剪切不稳定性发生以后,随着时间的进程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基于我建议的热塑剪切模型方程,直接切入这个现象的晚期和终态,阐明它的晚期演化和终态是什么样子。
沿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思路,我们发现,模型方程中的非定常惯性项,由于成为小量,在整个问题中,就可以忽略而出局了。如此一来,动量方程就使得在这个简单剪切的问题里的剪应力,在空间可以近似视为是均匀的了,虽然还可以随时间有缓慢的变化(由于热传导,温度随时间是会变化的)。这样,问题就变成了由热传导主导的演化过程了。
通过多次尝试,我们又找到了一条巧妙的“阴平小道”,最后就能得到一个基于一般形式的热塑性本构方程的、热塑剪切带宽度的一个积分表达了。
这条“阴平小道”包含两点:第一,把因变量温度当作自变量,而把自变量坐标当作因变量处理;第二,把通常的以应力作为应变率和温度等的函数的本构方程,改写为应变率是应力和温度为自变量的本构方程形式。这样再经过一次变数变换,唯一的涉及能量(热)的微分方程的一个二重积分形式的解析解就实现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前一个关于稳定性的工作,是本本分分地,按照流体力学的教科书,一步一步地推广到固体力学问题,从而得到了一些新结果的话;现在的做法,颇有抛弃常规、另出奇兵的味道:跳过实际的中间过程,把常规的自变量(坐标,应变率)和因变量(温度,应力)颠倒过来,等等。在和小俞及郑先生以及丁雁生(他帮助我做计算)的合作讨论中,我受益良多,觉得自己在研究技巧上变得成熟、机灵了许多!
1984年,我向在丹麦召开的世界力学大会提交了以上面结果为主要内容的论文,并被接受做口头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特别又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力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我的兴奋程度不可言喻。但是报告以后,反应平平,这引起我的反思。一是,这类骡马大会,规模太大,人太多,适宜开阔眼界,但是,真正的同行,反倒难以碰面交流了。第二,这类非常规的研究思路,不容易在一个小报告里讲清楚,即使是写成了一个二重积分的解析解,力学和工程界里做应用研究的人也不太容易接受,我需要将它表达成一个更加简明的形式!
于是,我将这个二重积分的结果,按照其中涉及的物理量的特征量,写成了一个简单的单项式,即热塑剪切带的半宽度大约等于热传导与特征温度的乘积与转化为热能的塑性功率的比值的开根!这样一来,热塑剪切带宽度的物理意义就变得非常简单清晰了:在这个宽度内,向外的热流,与作为热源的塑性功率,达到了动态平衡!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宽度就是热扩散的特征宽度,只是,相应的特征时间乃是:该区域内的热能与塑性功相持下,剪切变形的特征时间。
我把这个简单的结果,寄给了我在英国的老朋友Dodd,请他作为金属材料的专家,整理他手里的实验数据,来检验上述简单估计公式的正确性。他的结果是,根据他积累的不同的金属材料的数据,理论预估与实际观察的符合都非常好。 这使得我们两人都很兴奋,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短文,很快(1985年)就在一份材料杂志发表了,而且此后,得到了大量的引用和进一步的证实,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漂亮的二重积分的解析解!
这时,我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关于热塑剪切带宽度的结果,就是几年前的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普利高津(Prigogine,1917~2003)的‘耗散结构’的一个案例。这个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耗散结构”认为:在非平衡系统中,在与外界有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的情况下,复杂系统内各个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会产生自组织的有序状态,称为耗散结构。在我们的热塑剪切带的问题里,就是非线性的塑性变形向热的非平衡转化,与热耗散的相持,形成了准定态的热塑剪切带!
了解了这些,我既感到十分的振奋,又感到有些遗憾。振奋的是,普利高津花了几十年时间,又用了非平衡热力学等等费解的概念,才概括出来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结论;我作为一名科研领域的新兵,竟也能独立地达到了类似的结论。当然普利高津所涉及的对象要广阔得多,从化学震荡,到生命体结构,再到社会的组织等等。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努力探索的结果,别人已经在其它领域,得到了类似的、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这样,我们只是在工程科学领域的特定问题上,再现了别人的结论。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工程科学领域工作的人们,也能从我们工程科学领域的新问题出发,去推动解决那些困扰整个科学界发展的,那些更带根本性的问题!
不过,我所揭示的热塑剪切带的上述行为,也就是说,它是能量(热)扩散控制下的一种耗散结构这一点,在力学上还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在力学界大大有名、而且影响深远的Pradtl的边界层,其实,乃是动量(粘性)扩散控制下的一种耗散结构。再进一步,到了这个世纪开始前后,戴兰宏进入了非晶金属中的、纳米量级宽度的剪切带的研究。这时,我更进一步意识到,这乃是质量(自由体积)扩散控制下的一种耗散结构。由于质量扩散比动量和能量扩散都要慢得多,所以在近似的加载时间尺度下,这种质量(自由体积)扩散控制下的耗散结构,也就是非晶金属中纳米尺度宽的剪切带,也就是它们之中最狭窄的了!如此一来,依照扩散系数从小到大的顺序,考虑质量、能量和动量这三大力学规律,它们就分别对应于非晶中纳米宽的剪切带、金属中微米尺度宽的热塑剪切带,以及粘性控制下的更要宽得多(例如毫米量级)的边界层,对上述力学现象的这种系统化的比较、认识和理解,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上述工作还感到比较满意,感到欣慰的所在。
5.热塑剪切带斑图——剪切带间距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研究条件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善,我也被提了高级职称,可以招研究生了。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和我一起干活的研究生有曹银和、黄小玲、骆利民、邢达、薛青、卢春生、韩闻生、戴兰宏、凌中、胡春峰等人。
于是,我针对热塑剪切带的研究,着手从实验研究(黄小玲)、数值模拟(邢达)等几个方面,甚至针对研究问题,自己设计特有的装置(薛青),来全面研究热塑剪切带;另一边向下游,例如材料和工程等领域延伸。
那时,邢达结合黄小玲的实验结果,从数值模拟角度,全面再现了从均匀的剪切变形,在不同的扰动模式下,热塑剪切不稳定性的发生和发展;随着变形的进一步进行,它又如何发展成了晚期的处于相对准定态的剪切带。这个工作,对热塑剪切的演化和发展,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形象、完整的图画,这个工作,后来也发表在了JMPS上。
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还被一个、我认为的最后一个疑难所困扰:什么机制控制了剪切带斑图中的剪切带的间距呢?剪切带的间距,显然是,整个问题中的另外一个特征尺度,该怎么把它找出来呢?
我只好回到热塑简单剪切的原始方程组,这时我发现,当时为了研究不稳定性和剪切带的宽度,我把一个相对小了大约三、四个量级的一个无量纲量1/A<<1,完全舍弃了。但是,这种定义为应力的应变率敏感性与热传导之比的无量纲量A,恰恰就是流体力学里面十分重要的无量纲量Pradtl数,即粘性和热传导之比!
循着这个思路,很快我们就发现,在关于简单剪切下的剪切带的问题里,不是只有一个特征尺度(即剪切带的宽度),而是有两个特征尺度。而在这个一维的问题里,那另一个特征尺度,就只能是剪切带的间距。并且,这两个特征尺度之比,就是由这个Pradtl数的平方根所决定的。
后来,我们把这个结果拿到在希腊举行的一个纪念阿里斯多德多少周年的国际会议上讲了,还正式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因为是去希腊,我在报告和文章的一开头,就引用了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会的主席,Aifantis,很欣赏这个开头语,我们也从此结为了好朋友。
又过了十年左右,当我和Dodd在筹备新的一本关于剪切带的最新进展的综述著作,写到这个问题的时候,Dodd寄给我一篇他找到的在五十年代图灵(Turing)写的一篇关于Turing斑图的文章(1952)。其核心内容是:在一个包含两个要素的体系中,当每个要素随时间的变化(对时间的一阶导数项),都受制于反应(源项)和扩散(对空间的二阶导数项)两类规律时,两个要素的扩散率的差异,是该体系的形态的来源,例如斑马身上的条纹!Turing早在五十年代,甚至大大早于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就提出了两类有差异的反应扩散共处于一个体系之中是构成体系斑图的结论,是多么有先见眼光的科学思想和成果啊。我的上面那些结果,只是他所揭示的思想的一个实际工程案例,只是针对了两类重要的力学量:动量和能量的不同扩散(即粘性和热传导)的具体化,只是把这样的剪切带的斑图的特征,用无量纲数Pradtl数具体化了。
如前一节的结尾所述,我再一次感到,我不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再现别人的结论,我应该去努力开拓,去探索那些前人未曾涉足的、又有重要实际价值的新天地。我将在下一章,记述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探索。
(未完待续)
附件下载: